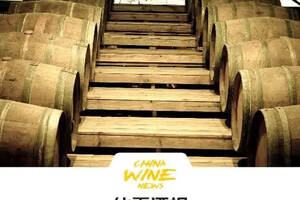古人饮酒,虽然是以酒为中心,但仍需菜肴、果品、点心等食物或是歌舞、美人、美文、美景等风月之物佐酒。
乐舞佐酒
周朝时就已经有了音乐佐酒的习俗。《诗经·唐风·山有枢》中说:“子有酒食,何不鼓瑟?”《诗经·小雅·鹿鸣》中说:“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到了汉代,宫廷宴会上,不但有正统的“雅舞”,还有来自民间的“杂舞”,并配以乐曲。以后,用音乐歌舞佐酒的风习,一直盛行不衰。
魏晋时期,琴酒之趣成为文人风雅,又尤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为代表。历史记载,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得琴酒之趣,忘土木之形。
唐代以舞佐酒之风更甚,杨玉环等皆以舞蹈成名,深受君王宠爱。到了宋代,又兴起了杂剧佐酒之风。《宋史·乐志》中记载,朝廷还专门训练出“小儿队”、“女弟子队”,遇有大宴时即令“各进杂剧队舞及杂剧”。
以花佐酒
唐宋以后,梅花作为一种意象,积淀了历代文人集体的审美经验,梅花佐饮(图3-34)也成为一种风俗。
南宋陈与义的《蜡梅》就描述了对这一意境的独特感受:“智琼额黄且勿夸,回眼视此风前葩。家家融蜡作杏蔕,岁岁逢梅是蜡花。世间真伪非两法,映日细看真是蜡。我今嚼蜡已甘腴,况此有味蜡不如。只悉繁香欺定力,薰我欲醉须人扶。不辞花前醉倒卧经月,是酒是香君试别。”
李清照的咏梅词在她的赏花词中所占比例最大,表现了以梅佐酒的高雅情趣。李清照《殢人娇·后庭梅花开有感》:“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楼楚馆,云闲水远。清昼永,凭栏翠帘低卷。坐上客来,尊中酒满,歌声共,水流云断。南枝可插,更须频剪,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
以书佐酒
古代许多文人一边读书,一边饮酒,以书佐酒,传为美谈。
宋朝的进士苏舜钦平日喜酒,他年轻时住在舅父杜祁公家中,每晚读书都要以酒相佐,量至一斗。杜祁公曾悄悄去看他读书,听见他读《汉书》读到张良使人袭击秦始皇于博浪沙时,可惜道:“惜乎,击之不中。”满饮一杯。接着又读到张良初遇刘邦于下邳,又感叹道:“君臣相遇,其难如此。”接着又饮一大杯。杜祁公大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以书佐酒,何等高雅!
还有,顾炎武曾在《与归庄手札》中写道:“别兄归至西斋,饮酒一壶,读《离骚》一首、《九歌》六首、《九辩》四首、士衡《拟古》十二首、子美《同谷》七首、《洗马兵》一首。壶中竭,又饮一壶。夜已二更,一醉遂不能起,日高三四丈犹睡也。”
以月佐酒
月下饮酒作诗最有心得的要数李白了,他有一系列有关月亮和酒的诗歌。
《月下独酌》中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
更有《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美食佐酒
袁宏道在《觞政》中总结道:“下酒物色,谓之饮储。一清品,如鲜蛤、糟蚶、酒蟹之类。二异品,如熊白、西施乳之类。三腻品,如羔羊、子鹅炙之类。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类。五蔬品,如鲜笋、早韭之类。”
《东京梦华录》卷四记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虽一人独饮,碗遂亦用银盂之类。其果子菜蔬,无非精洁。若别要下酒,即使人外买软羊、龟背、大小骨、诸色包子、玉板鲊、生削巴子、瓜姜之类。”历史上晋人毕卓更是“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蟹螯,左手持酒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为后人所乐道。
美色佐酒
在一千多年前,一些美女们就已经开始进行酒业促销、陪酒业务。宋代的大酒楼多以美色佐酒。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官营酒楼用官妓陪客:“每库(酒楼)设官妓数十人……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
私营酒家亦用私妓佐酒:“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玄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
宋代官场失意的大词人柳永的大半生都是在“美色佐酒”中度过的。他曾写过《鹤冲天》一词,抒发自己的感慨:“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