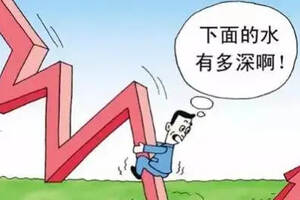醉眼看世间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人生短短几十载,要经受那么多的混杂与纷乱。有的人选择背负重担、直面生活的粗糙和真实,他们活得鲜血淋漓,但也活得清楚、明白;有的人选择躲开和逃避,他们或陶醉于书斋或沉醉于美酒,明明是入世之人,却活得像是出世的方外之人。我们无法简单粗暴地判定这两种生活方式孰优孰劣、孰高孰下,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我们可以不认可但是必须尊重每一种以不伤害他人为前提和目的的活法。

对于古人来说,在人间,饮酒,大醉,也是一种不受任何道德指摘的活法,更何况在古代那些朝代更迭或社会动荡的时代,人与天、人与世,到底是人醉还是天醉、世醉也是值得考量的。汉代学者张衡在《西京赋》中写道:“昔者大帝説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翦诸鶉首。”唐代学者李善注释:“喭曰:‘天帝醉秦暴,金误陨石坠。’”后世之人也以“天醉”象征世事混乱、社会动荡,“天醉”显然要比人醉要更加难以医治。

在“天醉”之时,那些沉溺于酒、逃避于世的人反而更彰显出了他们独特的风雅魅力。这其中的典型人物自然就是以阮籍、刘伶等几位“竹林七贤”成员为代表的的魏晋名士。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对酒》诗中写道:“所以刘阮辈,终年醉兀兀。”为何人要“醉兀兀”,其实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是“醉兀兀”而非几人之力可以力挽的了,他们的“醉兀兀”更像是一种清醒的、“眼极冷,心肠极热”的痛心旁观。
这种“醉兀兀”甚至可以不凭藉酒精的麻醉和催发就可以由内心蔓延开来,如宋代大诗人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中写道的:“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虽然口不饮酒,但那种热切之心早已让诗人的内心恍恍然如有醉态了。

在这些“醉兀兀”的人中,尽管他们在表面上有些许的不同,比如刘伶的终日任诞沉醉,嵇康那种近乎刚强的耿介,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最终结果是作为“竹林七贤”精神领袖的嵇康被司马昭以“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的罪名杀害,终年40岁。而刘伶则干脆完全自绝于主流,进入了一种以醉求醉,似醒非醒,超然于物外的状态,居然活了80岁。
一死一生,一刚烈一放诞。从结果上看,无疑嵇康更为高大。但我们不能因此而贬低刘伶,在人间醉酒而冷眼旁观也是一种“穷则独善其身”的难得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