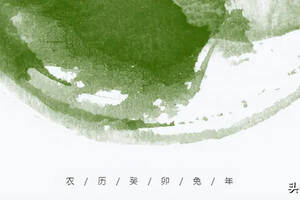编者导读:
不能不去追究,一个有着四千万人口,当时富甲天下,仅在宋夏边境一个方向就陈兵近三十万的大国,何以屡吃败仗,一战不如一战?又何以甘心容下这么不平等的条约?
今日的历史学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不仅以讹传讹地重复当时文官集团为推卸责任编造的谎言,还以一种貌似深刻的方式把问题推到了更为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通常见到了两种主要观点:
(1)自太祖朝以来的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得军队没有优秀的军人统帅,所以缺少战斗力。
(2)皇权高度集中,前方的统帅事事都要上奏,没有临机决定权。

宗仁宗永昭陵内院北神门
一句话,是自宋太祖以来,以加强皇权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导致了宋夏战争的失败。上升到“制度”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了!
但是,上述这两条结论是没有史实根据的。
第一,宋太祖虽然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剥夺了一些节度使的兵权,但还没达到“重文抑武”的程度,他重用的统帅还是军人出身的居多,如曹彬、潘美等。直到真宗时,镇边统帅还都是职业军人,以文臣镇边、书生典兵,是自仁宗朝开始的。而且抑文重武,主要还不是皇帝的意思,而是那些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的意思。(这一点我们后文还要详细讨论。)
第二,整个西夏战争期间,仁宗皇帝始终对前方边帅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多次许可他们“便宜从事”,所以,不存在事事都要向皇上请示汇报的事实。
如果是 宋代的君主集权制度导致了宋夏战争的失败,那么为什么比宋仁宗还要集权专制的汉武帝却胜利了呢?
够了,别拿“制度”这么玄乎的东西说事了;人办的事儿,就直接找人得了!
(二)
任何战争成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只在两个人身上,这就是双方的最高统帅。不管有多少人的军队,有多么复杂的环节,最终是由这两个人决定着数百万军人的命运的。
所以,追究宋夏战争失败的原因,只要以双方的最高统帅:宋仁宗赵祯和西夏王元昊身上找就行了。
了解他们的素质、水平、想法和做法,就能找到一切原因了。
记住,制度只是固化了的人的行为,人之外,没有制度。
所以,人不行,别怨制度。

(三)
从战略思想来看,元昊生下来就是要称王称霸的,为此,他的理性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建立起不再臣伏于大宋王朝的独立的大夏国家,他所领导的是一场西夏的“独立战争”,目标也是有限的,只是要获得宋朝的承认,而不是获得整个大宋的天下。他认为这个目标宋朝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发起一场又一场的进攻,逼迫宋朝承认他当皇帝的事实,他的目的最终达到了。
宋仁宗宅心仁厚,他认为“有生之民皆为赤子”,没有什么蕃汉的界限,为这么一个要独立称王称霸的个人野心打起仗来,不论汉人蕃人都要受罪,蕃人们悠然牧羊、汉人陶然耕织的幸福生活就会被打破,两族人民生灵涂炭,死伤枕藉,哭泣相闻,殊为不值。所以,在他看来,这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不打了,只要边境恢复和平,人民不再经受战争带来死亡痛苦,元昊要独立就独立吧,为了这一点,仁宗甚至连“面子”也可以不要的。抱着这种战略目的,他给范仲淹这些即将要开赴前线的将帅所下达的命令,居然不是努力杀贼,维护国家的统一,而是“有征无战、不杀无辜”,军队只是去威慑住元昊,而不是去消灭西夏军队的。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只要和平、不打仗、不死人,仁宗是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的。
元昊未必没有完全吃透仁宗皇帝的心思,对着这么一位“极仁主义”的皇帝,就是不动刀兵,长期耗下去,仁宗也会承认他的独立地位的。
但元昊不是和平主义者,无论有利于已的和平还是不利于已的和平,他都不接受。他只要战争,对每一个想称王称霸的人来说,战争本身就是目的,他们从征战杀伐中获得的快感远大于醇酒美人。他们以杀人为最高的快感,也不怕自己的人甚至自己被杀。元昊每战,必亲冒矢石,跃马阵前,别以为他是为了激励属下的勇气,才舍身冒险,做做样子的,不是,他是来享受作战快感来了。一切开国君主,都有这种血性: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大宋本朝的太祖,太宗皇帝,哪一个不是亲临前敌挥刀作战,身被创伤的。
说起来,仁宗皇帝命好,未成年的时候,有三位分别具有强悍、善良和奉献精神的母亲呵护着;成年后,宫内有着同样强悍的将门虎女曹皇后看着家,朝中有被他仁德感动的忠臣义士们护佑着。所以,他不仅没有上过一次前线,甚至毕其一生没有出过一次京城,这个成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乖孩子,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元昊在冰天雪地、尸横遍野的战场上享受到快乐与豪情。他讨厌战争,害怕战争,想以任何条件结束战争。
仁宗和元昊,从本质上讲就是两种不同生命禀赋的人,在天性上相互隔绝得太远太深,彼此绝对不能理解。仁宗总想以黎民苍生的生命和幸福来感动元昊,可元昊只想着再多打几个胜仗爽一爽,最好把仁宗抓来在帐前对他俯首称臣。
这两种人在战场上遇到一块儿,不用交手,就知道谁输了。

(四)
成败是由一系列具体环节构成的。对仁宗和元昊这两位最高统帅来讲,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两个,一是用人,二是办事。
先说用人。
元昊用的人都是“猛人”和“狠人”。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他依为股肱的党项本族人野利仁荣,这人是位大学者,创制了西夏文字。就这么一位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给元昊提出的居然是杀气腾腾、以战争立国的基本国策。他首先否定了对华夏文明的崇拜,指出:古来所谓“以夏变夷”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想当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国家强大起来,那不就是“以夷变夏”了嘛!作为一个国家立国基础的主流文化,应顺从本民族的自然天性而来,而不能生搬硬套别国的东西。固然要向别的国家学习,但一定要选择那些符合本民族天性、利于国家独立发展的东西。我们国家里,无论蕃人汉人,都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没有中原人雅好礼乐诗书的风气,我们只能顺应这种实际的民情,因势利导,进一步强化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满足他们的征杀欲望,同时赏罚分明,建立起严格的民法军纪。如果说学习华夏文化,也只应该学习商鞅使秦国强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不能学满嘴仁义道德、又拘泥于诗书礼乐等形式主义的儒家学说。这样才能使国家全体人民乐于征战,崇尚刚劲。如此,方可以钳制中国、统驭戎夷,那些斤斤于言礼言义的宋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元昊极其倚重野利仁荣。野利仁荣于宋庆历二年秋天去世,元昊曾三次前往吊丧,恸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
元昊重用的另一个人是汉人:张元。张元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只是姓张而已。他原本是陕西华阴一介书生,自负其才,屡试不第后,曾和他的一位姓胡的朋友赶往边关,他们雇了几个人拖着一块大石板在前面走,石板上刻着他人两个人嗟叹怀才不遇的诗句,他们两个人跟在后面,吟诗大哭,希望以此引起边关统帅的重视。那位边关统帅还真接见了他们,引他们入大帐聊了一阵儿,大概是觉得话不投机,又把这两人送了回去。回到家乡后,不知为什么事,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这次侮辱让他下决心投靠西夏。临行前,路过一个不知什么地方的项羽庙,“乃竭囊沽酒,对羽极饮,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刘项起吞并’之词,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看来,张元不是毫无忠君爱国观念的人,他只是太个人主义了,他知道自己的才干远高于朝堂之上那些庸碌之辈,有这些人当政,他永无出头之日。他太欣赏自己生命品质的优秀,不能忍受在平庸的生活中,耗尽这天赋的优秀生命、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寻找一切机会证明自己的优秀,为此,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国。为此,他极为痛苦,这才有“悲歌累日,大恸而遁”的情况发生。人们当然可以谴责张元的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国家不用你,你也不能叛国呀!但从实际后果来看,一个不能真正吸纳本国优秀人才的国家,注定要衰亡下去的,战国时期那些被秦国灭掉的国家不都是如此吗?
张元是和他的胡姓朋友一起到的西夏的,在那里,他才改名叫张元,那位吴姓朋友改名叫胡昊。两个人终日在西夏都城的各大酒馆喝酒,饮后在墙上题诗,署名张元、吴昊。两个人的名字连起来读就“元昊”,这在当时是冲撞国王名讳的违法行为,他们俩想借此引起元昊的注意。果不其然,没过两天,他们被抓了,元昊亲自审问说:“你们两个是从大宋来的人,应该懂得不能冲撞本王名讳的规矩呀,为什么这么做?”张元反唇机讥:“违了你名字的讳有啥了不起的,有的人连姓都不顾呢!”这正戳到元昊的痛处,他们的本来没姓,自己造了个北魏鲜卑的姓:拓跋;后来归依李唐王朝,皇帝赐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赵家皇帝赐姓“赵”,实际上等于无“姓”之人。元昊听出了话外之音,不以为忤,反引两个人入室深谈,甚为投机。张元得到了重用,不到两年,就当上了元昊的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元昊攻宋的许多谋略都是张元提出的,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都有张元参谋赞画之功。元昊那句“朕当亲临渭水,直据长安”的豪气干云的通告,也出自张元的手笔。
仁宗“仁”啊!张元叛逃西夏,屡献攻宋之策,仁宗都没有缉拿他的家属,反而赐其钱米,希望张元能被感动,回头是岸。这位宅心仁厚的皇帝永远不能理解那种心身负奇才又野心勃勃的人的心理,他们一心只想使自己生命优秀的天赋本质得到实现,而对寻常人会感恩戴德的仁心惠意不屑一顾。张元没有回头,不仅从行为上没有回头,而且在精神上更为决绝。按他的理想,是想彻底灭掉大宋的江山,让满朝堂那些曾瞧不起他的庸碌之辈,彻底品尝漠视他的苦果。元昊都没这份野心,当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与宋朝和谈时,张元坚决反对,等到元昊与辽国开兵打仗,张元知道西夏已经永远没有灭宋的机会了,他彻底绝望了,终日对天咄咄叹息,没几天,就忧愤而死。
这是那种为自己的优秀而活、也为自己的优秀而死的人,这种铁石心肠,是任何恩惠都无法动摇的。
野利仁荣和张元之死,对元昊的打击很大,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是由一个英雄团队共同干出来的,这两个人才的早逝,使元昊失去了能克制他弱点、发挥他长处的左膀右臂。自这两人殁后,元昊再也没有做出过更为惊天动地的大事。
再看宋仁宗的用人,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和他气味相同的仁人君子,另外,还有少数摸准了他的脉,伪装成仁人君子的小人,所以,可以说他用的人都是“仁人”和“佞人”。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
以夏竦、韩琦、范仲淹为例。夏竦聪明,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但自私,不敢坚持原则;韩琦坦荡磊落,在朝廷内部的权力角逐中,秉公守正,坚持原则,确是一位良相之才(详见韩琦小传),但心肠软,受不了战场上血腥的打击,而且缺乏真正的军事韬略,其军事建议是自己都执行不下去的夸夸其谈。范仲淹个人道德素质优秀,体恤民众,在和平年间,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地方官,可是,见解卑陋,议论迂腐,他与仁宗之间的相知,完全在于共同拥有一个“仁”字的心理相通。他深知仁宗的心理,所以提出了被奉为国策的防守战略,当仁宗与西夏媾和时,他是欢欣鼓舞的。其实,早在1042年(宋庆历二年)五月,定川寨战役之前,宋夏两国边境拉锯战正酣的时候,他就向仁宗皇帝提出与西夏议和的建议,说:“兵马精劲”是西夏的优势,“金帛丰富”是大宋的优势;西夏人依仗其优势,是不会听从我们的仁义教诲的,而我们又不想大动干戈,与敌人打仗。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金钱买和平,多给西夏人“金帛”,以换得休战。他还举自己当越州知州时的财政收入为例,说仅越州一地一年的税收就值绢三十万匹,足以够支付对西夏一年的“赏赐”了。
初读到这种建议,让我们瞠目结舌,这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千古名臣为天下“忧”出的道理吗?这是什么道理?人家来打咱们,咱们不还手打人家,还要给人家“钱帛”,换得人家不再打咱们!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凭什么给敌人这么多的钱?
范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说,这样虽然使越州人民受了些苦,可是天下不打仗了,可以少死多少人呐!
我无言,这也是由其天赋的生命本质所造就的意见,不可沟通,不可更改。我只是在努力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或许是某些孩子被绑架了的父母,害怕绑匪“撕票”,不敢报案,想拿钱给绑匪“私了”的心态?
这种人是不能镇边打仗的!
除了韩琦之外,夏竦和范仲淹两人其实都不愿意在外镇边,夏竦削尖脑袋走后门想调回京城,范仲淹也屡次上表以身体原因辞掉边帅之职。他们的文才都没得说,十分优秀。范仲淹镇边期间,留下过一首著名的词《渔家傲》,其中的下半阙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言辞精到,意境悲凉。但确不是他的职务及所处的地位该发出的声音,作为镇边统帅,应该高歌“马蹀於氏血,旗枭可汗头。”怎么能发出如此悲凉颓废的韵调!主帅如此,全军的士气可想而知。
(五)
人不行,办事就不行!
先从事关每次战役成败的情报问题说起,我们已经知道,元昊出色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能力是他每次战胜的重要原因。宋仁宗也意识到情报问题的重要性,他多次下诏要求在边境重金收买掌握西夏情报的间谍,还下诏,要求缉拿、诛杀已潜入京城汴梁的西夏间谍,但从未收到任何实效。宋军从来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就是在战场上,也少有过准确的战役情报,甚至到打完仗了,还不知道对方的真正人数。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不肯真正花高价钱买情报,二是情报送到眼皮子底下了也不会分析。
再说用人政策。宋仁宗也知道“人才决定成败”的这个大道理,所以,多次下诏让各级官员推荐能领兵打仗的人才,为了吸收人才,他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仁宗一朝科举取士的人数比前朝增加了一倍还多。在仁宗的激励下,几乎所有科举出身的文官都喜欢上书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奏书超过万件,绝大多数的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选拔优秀的人做边帅”。但是,没有一个人明确建议,谁可胜任优秀的将帅一职,这些话是些正确的废话,有时连宋仁宗都腻味了这些空话,下诏警告说:大家不要指望靠提边防政策建议而升官。
从上到下,每个人都高喊重视人才,可怎么就没真弄出个人呢?难道堂堂大宋四千万人口,就没个能带兵打仗的人才?当然不是,宋朝是有人物的,曹玮、狄青,论韬略,机智与勇气,都堪为帅才,用之得当,是可以与元昊一较雄长的,可惜,终其一生,仁宗皇帝没有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与元昊放手一搏。
没有人才的根子问题,还是在仁宗身上,他按自己的鉴赏能力重用的人,都是夏竦、韩琦、范仲淹这样的人,再由这些人去发现新的人才,这些人自然又会推荐自己看得上眼的人,如此下去,以发掘人才的名义,官员队伍人数越多,寻找优秀人才的调门越唱越高,可是庸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真正的人才的出头之 路逐渐被彻底堵死了。仁宗还有个“言论自由”的优点,大开纳谏之门,让这些庸人提建议。这些人提的建议都和夏竦这些人差不多,初看起来都挺有道理,但由于缺少对自己建议所能产生的实际后果的深刻洞见,他们的政策被采纳实施一个阶段后,就暴露出问题了,又只能再停止,这就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现象,像前面所讲过的潼关城的“修与拆”的例子不计其数。
总之,宋仁宗的“扩招”政策和“纳谏”政策,造就了一个数量空前庞大、又放言无忌、不负责任的文官集团,对大宋王朝来讲,这是个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这个文官集团形成的标准就是庸碌,只有通过刻板庸碌的科举门槛才能进入到这个集团中;这个集团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是共同迫害不接受他们庸碌规则的优秀人才,张元不得重用,被迫叛逃就是一例。要知道,这种人才,损失了一个,几乎等于损失了半个国家。名将狄青也受过这种“迫害”,韩琦就曾当面羞辱过他:“会打仗有什么了不起,考上状元在京城东华门外被唱榜的人才是真正的好汉!”狄青出身行伍,是从士兵一路拼杀到大将的,按当时宋的军法,士兵均要在脸上刺字,皇帝提拔狄青做了枢密副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狄青可能也是仁宗朝唯一以武将身份做到这个位子上的人)时,建议他把脸上的刺青去掉,狄青自豪地说“不必去了,我要让天下贱儿,知道国家有此名位相待。”然而没有多久,文官集团对他的攻击就接踵而至,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只能编排“五行变异”这些迷信现象来罗织罪名。仁宗皇帝起先还为狄青开脱说“狄青是忠臣”,当时的宰相文彦博(这人也以贤明著称)顶了一句“太祖不也是周世宗的忠臣吗?”仁宗皇帝退让了,同意把狄青贬出朝廷,到陈州当知州。狄青气不过,找到宰相署衙,问为什么无罪而被贬。文彦博两眼瞪着他许久,才吐出一句话:“无他,皇上怀疑你。”这是那个时代文官通用的官场伎俩,明明是他本人怂恿皇帝贬谪的狄青,这时又把责任推到皇帝头上,而后来做史的文人,只记住这句话,以讹传讹,就真认为是皇帝提防武将,才有抑武重文之事。狄青到任后,朝廷每月两次派内侍来“抚问”他,他是位直肠热血的军人,受不了这种狭隘的猜忌,不到半年就忧愤而死。
狄青的遭遇反映的问题,是这个文官集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群体利益,尽管他们内部有“党派”之争,但在遏制军人权力上,立场是一致的:北宋的重文抑武其实只不是皇帝推动的,而且也是是这个文官集团推动的。他们天天在皇帝面前以关心皇帝的切身利益为由,编造武人拥兵自重、图谋造反的段子来恐吓皇上,其真实的目的是扩大文官集团说话的权重。正好又碰上仁宗这个智力正常、但缺少超群的洞察力和驾驭力的平常人,于是文官集团日益强大,利益也越来越多。范仲淹的“守势战略”和“求和主张”之所以得文官集团的广泛拥护,也反映出这个集团独特的利益诉求:要长期持久防守,就要大动土木,修建防御工事,这不正是前方那些知州、知县们大捞银子的好机会,而求和就不用真打仗,显不出他们这些文官的无能,何乐而不为!到后来,这种集团利益已经板结成无法攻破的堡垒,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集团利益打压下失败的。宋以前,人们只看到了武将专权带来的藩镇割据之害;自宋以后,文官集团的小团体利益诉求对国家造成的危害至今还少有人认识到,实在值得深刻反思。
当然,得特别说明一句:不能以身份论水平,不是文人出身的人都不会打仗。曹操是位大文学家,可也是杰出的军事家,汉光武帝时的大将邓禹、冯异等,都是文人出身,仗打得也同样出色。笔者的意思是说,不是不能用文官来做镇边统帅,而是要用有军事才干的人去当统帅,不论其原来是当兵的还是学文的。宋仁宗的问题在于用的都是庸人,之所以我们用“文官”或“文人”来代称这些庸人,是他用扩大了的科举考试手段,把这些庸人变成了“文人”或“文官”,而不能被变成“文人”的人就不能被重用。
(六)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检讨范仲淹的防御战略,是绝对的“臭棋”。筑堡连线,分散驻兵,有警来袭,互相救援。从直观印象上好像颇有道理,但其实际作用只应付边境上的小规模冲突,一旦遭遇敌人重大的战略进攻,立刻就显出劣势,这一战略的消极后果,在前面关于三场战役的总结中已有过具体分析,不复赘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长期持续的消极防守的战略,消耗了国家大量的财力;兵员人数势必越来越多,国家要防守的要塞越来越多,军费开支也必然越来越大,人民负担越来越沉重。最关键它还在于从根本上毒害了军队,把本来用于打胜仗的武装集团变成了一个磨洋工、骗兵饷、两头讨好处的兵痞集团,这一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等到金人崛起,发动对宋朝的战略进攻时,宋朝的军队早已丧失了以武力捍卫国防的能力,反而变成了乘机抢掠本国民众的武装团伙,大宋朝须臾之间土崩瓦解。
其实,作战的精义不在于教条化的“攻”与“守”,而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元昊也打过防守仗,那是在1044年(宋庆历四年)九月,辽兴宗发兵十万进兵西夏。面对强敌,元昊避退三舍,每退三十里,就将沿途所有田园烧尽,使辽军人无粮吃,马无草喂。同时,不断释放“求和”烟幕,麻痹辽军斗志,待辽军人饥马乏之时,突然全线出击,大败辽军,斩获无数,连辽兴宗本人都差一点做了俘虏。这才是真正的积极防御战略。这种天才,是范仲淹那平庸的头脑中永远也想像不出来的;这种凶狠决绝,是韩琦那脆弱的心灵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
我又想起了张元题在好水川的那首诗!
(七)
公元1063年(宋嘉裕八年)三月,宋仁宗病逝,年仅54岁。死后庙号被封为“仁宗”,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仁”字谥号的皇帝。
但他留给国家却是一笔极其沉重的政治经济遗产:
(1)庞大的财政赤字,自1041年(宋庆历元年)始,国家财政赤字每年都在300万贯以上,到1065年(他去世不到两年时),赤字额已达到一千五百万贯。
(2)官员队伍恶性膨胀,仁宗朝比真宗朝的官员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政府开支也随之增加。
(3)军队人员急剧增加,到仁宗去世时,宋朝的军队兵员数量居然是太祖开国时的5.3倍,军队开支竟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而且,这支规模空前巨大的军队,居然没打过一次象样的胜仗。
这才是那个“仁”字所蕴含的全部份量!
做好人,是要付代价的!
这种沉重的包袱造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后来的神宗皇帝再坚决,王安石再聪明,也无力回天了。
1022—1063,仁宗在位的41年,在一团和气、交口称赞的仁德之中,大宋王朝进入了不可挽回的沉沦之中。

(八)
公元1052年(宋仁宗皇祐四年),名臣范仲淹去世,《宋史》记载:“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西夏“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1063年,宋仁宗逝世后,派使节通知辽国,当时辽国的皇帝是辽兴宗,闻讯后沧然涕下,说:天下又要打仗了。
初读这些记录,我的心里充满感动,觉得范仲淹和宋仁宗以仁德为核心的人格魅力,居然感动了敌国的人民和君主。
现在再读这些记录,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如果范仲淹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悍将,宋仁宗是雄才大略的明君,他们的死,应让敌国君臣额首相庆才是。可如今,敌国臣民是为他们的死流下了眼泪,但那不是感动的泪水,而是恐惧和担心的泪水:这些文弱的人都死了,万一上来一拨强悍的人来打我们怎么办?
而我们自己,是不是感动太多了一点,这感动让我们眼里常含泪水,这泪水又模糊了视线,使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和本质。
巡行于当年宋夏边境的古寨堡之间,遥想黄土层中尚存的累累战士尸骨,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Ω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休闲读品杂志社微信:xiuxiandupinTX